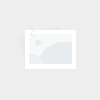把伤痕当酒窝
- 文学经典心理疗愈
- 2025-06-30
- 131
老家巷口的王奶奶总爱坐在青石板上,用指甲轻轻刮过木凳上那道蜿蜒的刻痕。那是三十年前她男人修屋顶时,梯子打滑撞出的裂口,如今木纹里积了岁月的烟尘,却像一道笑纹,在午后阳光里泛着温润的光。伤痕这东西,若盯着看它流血的模样,便只觉疼;若等结痂了再瞧,或许能看见时间在上面绣了花。

年少时摔断过胳膊,石膏拆掉那天,小臂上留了条浅粉色的疤,像条蜷缩的小蚕。我总拿袖子遮着,生怕同学指着它问“怎么弄的”。直到有次看见同桌膝盖上狰狞的旧伤,他说是学骑自行车时栽进了碎石堆,边说边笑出眼泪:“你不知道我妈把我拖回家时,我裤腿和血痂粘在一起,脱裤子像撕纸一样响!”那道疤在他掀起裤腿的动作里起伏,明明是道旧伤,却成了他讲笑话时最生动的注脚。后来我不再藏着胳膊上的疤,当有人问起,就学着他的样子咧嘴笑:“爬树摘槐花摔的,你猜我最后摘到了没?”
去年冬天遇见楼下的阿哲,他刚从工地回来,羽绒服袖口磨出了毛边,手背上有道新伤,是钢筋划的。他搓着冻红的手笑:“昨儿扛钢管时没拿稳,差点把自己钉在架子上。”我问疼不疼,他却掀起另一只手,掌心里密布着深浅不一的老茧,像块被反复打磨的皮革:“你看这些疤,刚有的时候都以为要了命,现在摸起来糙是糙了点,搬砖倒更稳当。”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手背上的新伤在夜色里泛着微光,像一枚被擦亮的硬币。
人总爱把伤痕当伤口,想着结痂、愈合,最好能彻底消失。可哪有什么真正的消失呢?就像老家那棵老槐树,被雷劈掉半棵树干,剩下的半边却年年开花,树心空了的地方积了雨水,成了麻雀的饮水池。那些疼痛过的痕迹,其实是岁月盖在生命上的邮戳,寄走了脆弱,寄来了韧性。当你能指着一道疤笑出声时,不是忘了疼,而是把疼酿成了故事的下酒菜。

王奶奶的木凳后来被虫蛀了,儿子要扔,她却抱着凳子掉眼泪:“这道痕是你爸坐出来的,他走那年,我摸着这道痕想他,摸着摸着,就觉得他还坐在我旁边。”现在那凳子放在她床头,刻痕里插着一束干花,像给岁月的酒窝别了朵花。原来伤痕从不是需要掩盖的伤口,而是生活在你身上按下的指印,当你学会对着它微笑,它就会变成嘴角扬起的弧度,盛满星光。
本文由鹑火于2025-06-30发表在哲思生活实验室,如有疑问,请联系我们。
本文链接:https://www.izhufei.com/post/8.html
上一篇
三十而立吗?